“明变求因”:一种保持开放性的研究范式
- 国际
- 2025-04-10 16:30:05
- 17
陈广宏教授《竟陵派研究》已于202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下文引述本书內容,仅随文标示页码)。《竟陵派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于2001年,2006年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本次即是据2006年修订版的再版。

《竟陵派研究》书封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万历中期以后的政治与学术;第二章嘉、隆以来文学风气之嬗变;第三章竟陵派发韧期: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第四章竟陵派成立期:有声两都间与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第五章竟陵派发展前期:《诗归》盛行与“竟陵一脉”成为时响;第六章竟陵派发展后期:谭元春于竟陵派影响的进一步拓展;第七章竟陵派的文学思想;第八章竟陵派的文学创作。因此,总括起来,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第二章为竟陵派形成的背景分析,第三至第六章为竟陵派形成历程的梳理,第七、第八章为竟陵诗学的综合论述。第二部分构成了第三部分的论证基础。
相较于2006年版,此次再版除补入最新研究成果、检核订补引证材料、润改个别文字等技术性、细节性改动外,“框架结构未变,论述的角度、观点未改”(本书“新版后记”),基本保留了原貌。之所以如此,如作者所自言,“即便自悔少作,毕竟不是重起炉灶新写一书,就此留存一个样本,作为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受训练的见证”。此为谦辞,但也是真实的表达。
作者心目中的“一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受训练”,主要在关联密切的两个方面,一是“中观研究”,就本书来讲,就是诗歌“流派”研究,二是“明变求因”的研究方式。
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流派”研究,可溯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派别”研究(如梁昆《宋诗派别论》)和流派代表作家的体派研究(如张大东《中国文学上之“体”与“派”》),其成为一种自觉、普遍的研究范式,则缘于1980年代程千帆先生倡导的诗派或诗人群体研究。作者在本书“新版后记”中回溯这一历程时谈到“流派”研究作为一个研究热点出现,其所具有的标识性意义:它意味着与“五四”以来学术现代化历程的一种接续,“表明文学史研究重又回归实证的立场,回到朗松所说的‘达到客观的事实’为第一要务,并且有了文学社会学的加持。”因此,“流派”研究是同时指向实证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传统的成熟的作家研究、文艺思潮研究等可在“流派”研究的范式和框架下“重新构建模板”而形成某种学术上的突破(684页)。类似的表述也见于作者其他著述,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追求。
不过,作者选择中观研究、流派研究,除感染于时风,主要地还是与他自身的学术训练和研究经历有关。作者对竟陵派硏究的关注,始于硕士学习阶段,其硕士学位论文就是《钟惺年谱》(该《年谱》后收入章培恒先生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完成《钟惺年谱》后,作者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沿着《年谱》留下的线索,按照地域对万历中期以来与钟惺、谭元春相关的作家群体及其文学活动加以梳理、考察;二是重新细读钟惺、谭元春作品,力求准确把握其作品的内蕴及风格上的特点,同时对谭元春的创作和重要的学术著述做了相应的系年(678-679页)。这样,作者研究的视野就自然由钟惺逐渐覆盖谭元春及受钟、谭影响的各地诗人,而对钟、谭作品的准确把握,则在基本层面上,建立起学术与文学等影响、关联、比较研究的基础。
此种学术经历,使得作者对所谓文学“流派”有了历史的、生动的认识,同时也必然促使作者切实思考流派与作家个体创作、文学观念的关系,与文艺思潮的关系;思考流派这样一种中观研究,较之一般文学史研究,会在何种层面或方面触动文学史研究,以及以流派研究介入文学研究,其可能的阐释力,其所揭示的文学史所具之风貌、特征。而实现 “诗派”研究目标的基本方法,作者归之于“明变求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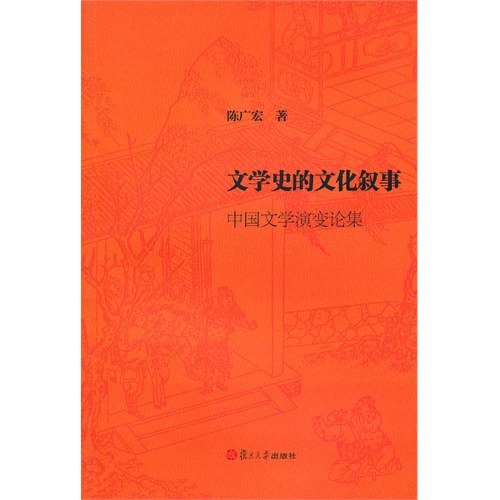
《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进论集·自序》书封
“明变求因”严格说来并不是特异的研究方法,但对于作者来讲却具特殊意义。作者曾在多个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过“明变求因”的意旨,如《文学史的文化叙事:中国文学演进论集·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即谓:“(《文学史的文化叙事》)试图深入中国历史上极为丰钜而独特的文化形态,建立对诸多事象(包括域外产生的影响)的考察与阐述,即便是从单一的作家、文体、现象入手,亦希冀在展开的文化构造关系中,探究其相对长时段的生成、演化及重要关节转捩。”作者并将此种文化学的倾向与作者接触古代文学研究时盛行的“文化热、文化研究的持续传入以及史学观念的渐次变化”联系起来。作者多次引用蒋寅先生提出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所谓“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即在充分占有并梳理大量当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各种复杂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做比较全面的历史复原工作,考察其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使文学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去。并且,举凡文学理论、风格、文体等问题的研究,皆可在一种历史还原中把握其演变的轨迹。明清文学领域得天独厚的资料条件,不仅使得这种‘进入过程’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也赋予了该领域研究者这样一种职责。不管有没有做到,我把这样的文学史研究视作工作的目标。”(第679页)“明变求因”的研究也就是“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是一种以历史还原为依归,以文学事象梳理为中心,结合多方面因素,容纳文学理论、风格、文体等,并在文献特点上洽合于明清文学的综合性研究方式。此种综合性,使其自然地对前面提到的实证和文化研究形成支持。因此,作者在前引“新版后记”中回溯了流派研究后,总结说:“概而言之,那个标记我们成长的年代,所谓‘明变求因’,几乎构成大家研究习得的认识论框架及学术合法性的由来。”“明变求因”代表了作者最初的也是最具范型意义的研究方法,而《竟陵派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整一性,体现得特别典型。
二
若析而言之,从“明变”一方面讲,“明变求因”体现在本书对竟陵派形成、演变历程之梳理、描述细密、扎实、准确。本书不仅在大的节点上梳理了竟陵派从发韧期、形成期到发展前期、发展后期的演变过程,而且每个时期都有合理的细分。比如钟惺、谭元春早年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文学交往,向不为研究者所注意,但本书围绕钟惺与黄玉社诸子交往期间撰作的诗学名篇《与王稚恭兄弟》,结合黄玉社与公安袁氏的接触和联系,敏锐把握到,《与王稚恭兄弟》无论对江盈科诗的批评还是对王应翼兄弟的警诫,都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明确宗旨,“其讨论的内容恰恰就是他们当时极为关切的共同话题,关系到他们对公安派为代表的诗歌新变走向及其利弊的重新估价,以及对自己创作道路何去何从的执定”( 第181页)。正是在此种讨论中,钟、谭诗学观点、立场“愈来愈走向明晰、坚定,一步一步接近他后来成熟的主张”(第183页)。所以,作者把钟、谭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文学交往看成是“竟陵派文学的发端”(第174页),“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第183页)。这就为竟陵派形成树立了一个清晰的起点。
再如本书论述竟陵派形成期时,细分出竟陵派在南京、北京的传播、影响,特别是据《隐秀轩集》文集刊刻情况和作品收录情况,钩稽出天启二年(1614)《隐秀轩集》中存留之1610年前诗和1610到1614年诗,更进一步将钟惺今存1610年至1614年九月与谭元春同游西陵前所作约240首诗,再分为三个阶段(第242页),通过分析比较,确证“自庚戌(1610)这一年始,他在创作上确实已确立起一种自具精神面目的特异风格”(第247页),1610年就成为钟惺诗文创作“自新的一道界碑”(第236页)与“钟伯敬体”形成之标志。
过程梳理之细密,有利于发现之前研究忽视的重要节点,也有利于纠正一些重要的认识偏差,从而带来对竟陵派形成历程的准确描述及相关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准确把握。如学界一般认为雷思霈对钟惺有重要影响,但本书基于对钟惺诗学历程的清晰把握,认为在雷思霈以座师拔擢钟惺之前,钟惺诗学见解已较为成熟,诗风颇近公安派的雷思霈在诗歌创作及文学主张上已不可能对钟惺产生多大影响(第233页)。与雷思霈相对的是蔡复一。本书充分考察了钟、谭与蔡复一围绕《诗归》评点的讨论,指出“蔡复一不仅仅是竟陵派影响的接受者”,“他对钟、谭所代表的竟陵文学从理论建设到创作实践都曾有积极的参与和贡献,因而在竟陵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其他同志所无法比拟的”(第293页)这样的论证所带来的过程及问题衔接、贯穿的紧密性,不只保证了竟陵派形成过程中节点确定之坚确有据,同时呈现了竟陵派有机凝结的过程,“竟陵派研究”也就不是钟惺、谭元春叠加的研究,而确实是作为一个“诗派”的整体研究。
从“求因”一方面讲,“明变求因”体现在对背景或影响因素发掘、论证之切实、不肤廓。比如该书在论述“嘉、隆以来文学风气之嬗变”时,着重论及 “嘉靖八才子”及由之分化出来的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崇道派和李攀龙、王世贞“后七子”对竟陵派的影响。作为竟陵派形成的文学史背景,本书无论论证哪一个时期文学思潮与竟陵派的关联时都抓住了切实的关联。其论唐宋派在“精神”这个思想和文学观念上对钟、谭的影响,是深心体会的新见。又如谈到“后七子”复古思潮时,本书一方面注意到了后七子极端复古的诗学对于公安派、竟陵派所带来的物极必反的效应,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本书同时注意到了虽立场相左,但“后七子”与公安、竟陵在所处理之诗学问题上的一贯性,如本书所言:“他们(“后七子”)所致力探究的也确实关涉古典审美最为核心的问题,虽然没能在他们手上获得很好的解决,但他们的努力本身仍在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第141页)明代诗学尤其是“后七子”之后各派在出奴入主的攻讦中相反亦复相承的复杂关系,前辈学者如郭绍虞有所论及,但求其在长时段流变中结合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研究,本书应是较为突出而值得重视的。
钟惺、谭元春的心学、佛禅的素养是本书一直强调的思想因素,本书准确把握了钟惺“将阐玄理、证实相视为文学表现的一个较为根本的职能”(第485页)的文学观之“形上”特征,从钟惺“以道情禅观对之(山水、自然)”(第485页)的哲学观物方式和审美观照方式切入,指出:“这种审美观照方式给竟陵派文学创作带来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突出表现对幽孤之境的内省体验。”(第485页)而更内在的,此种由山水而玄思的文学表现形式,直接构成了钟、谭山水游览一类的诗歌呈现谢灵运式的“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的体式结构特点(第493页)。同时,置于整个诗史和诗学思想史的演变,本书更抓住钟、谭重“清思”、“名理”的特点,比较“以道情禅观对之(山水、自然)”与晋宋玄言、山水诗“以玄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方式的一致性,沟通了此前论者有所忽视的竟陵诗风与晋宋间文学趣尚的内在关系(第480页)。一方面是重要事象、细节呈现,一方面是与历史语境的深度连接,都是基于对钟、谭思想、创作的系统结构上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与文学间建立起实在的联系,且生发出一些重要的、具启发意义的问题。
本书“明变求因”之细密、切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相关研究的积累等,但最重要的可能仍要归结到作者前期的学术训练、学术准备,尤其是《钟惺年谱》及《谭元春简谱》《钟惺、谭元春文学活动系年》的编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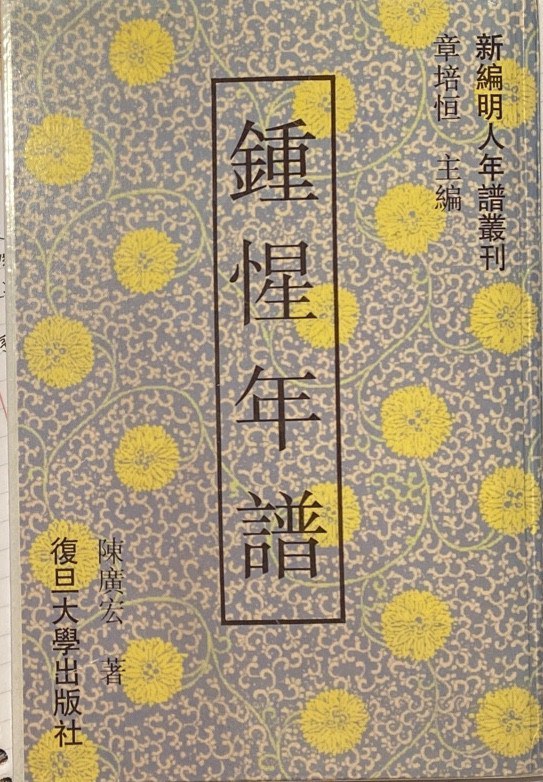
《钟惺年谱》书封
《钟惺年谱》等的写作对于《竟陵派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文献上的,这包括具体的版本文献梳理的普遍运用,前举该书对《诗归》及对竟陵派受影响于《文心雕龙》的论述,皆是其例;也包括整体论证中文献之密集、多方取证之绵密、审慎,这集中体现在本书对钟惺、谭元春早期文献的钩稽和运用。钟惺早期作品《玄对集》《简远堂集》等皆已散佚,故学界对之鲜有论及。本书通过梳理《玄对集》结集时间,推定“集中诗文绝大多数为钟惺早年在家乡所作当无疑问”(第185页);通过对沈德符《谭友夏夜话》所透露的谭元春对《玄对集》的评价及对所谓“玄对”之意的分析,不但揭示出钟惺早期斥伪尚真、反对时趋的诗学要义,而且揭示出钟惺“试图通过此种关乎虚静体道的思想方式与审美经验,在诗人心性与诗境之间重新探讨一种契合关系”,而此种努力“无论对他下一阶段诗学理论以‘平心静气、虚怀独往’的要求改造‘性灵’学说,还是对其所谓‘深幽孤峭’诗风的开展,皆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第188页)。本书并且通过李维桢对《玄对集》与谭元春的不同评价,牵引出钟惺早期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的不相一致或矛盾性的重要命题(第188-189页)。同样的,本书也通过仅存的钟惺《简远堂近诗序》和谭元春的《题简远堂诗》,抽绎出“清物”的审美范畴和“灵”“朴”创作技巧,进而梳理出从“灵”“朴”到后来的“隐秀”及“期在必厚”的诗学理路(第191-194页)。此一理路构成了本书第七章“钟、谭的诗学观念”研究的基本脉络、框架。本书所自陈的“着重考察这些观念的理论性质与内在肌理构成,并揭示它在文学思想历史上的演进脉络”(第365页)的文学理论研究宗旨,也由此得到充分体现。此类同时具有绵密梳理与跃动之穿透力的论证,是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假如没有《年谱》写作所积累的文献排比、缀连作为基础,这些细微但重要的问题不易捕捉也不易征实,而重要问题之间的贯穿和跳跃则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且错乱无序。
二是区域、交游上的。《竟陵派研究》几乎对钟惺、谭元春所历地域所有交游作了细致钩稽、考证,尤以历来被称作“人文渊薮”而竟陵派影响曾持久盛行的江浙地区及福建地区最为深细。本书论述竟陵派发展期时,首论 “钟、谭在南京的拓辟”,梳理出钟、谭与林古度父子、商家梅等以曹学佺为中心的游居南都的闽籍诗人交游圈,通过林、商诸人诗风向竟陵的转变,本书指出:“正是钟惺以其独具风格的创作与主张,一点一点地变易南都诗坛那种在曹学佺身上体现得颇为充分的绮丽清新之六朝初唐宗风,使得曹氏及其创作终于没能产生‘靡天下以从之’的效应。”(第207-208页)钟、谭与南都闽籍诗人的较为固定的基本交游圈,也因此“构成了竟陵派在南都文坛谋求发展的一个基地”( 第211页),竟陵派的所谓“成立期”正是以此为发端,而林古度、商家梅之追随钟、谭入楚及其进一步向奇奥幽峭诗风的转变,就成为“竟陵派成立并产生影响的一个见证”(第249页)。对于引导了竟陵派后期发展的谭元春,本书同样详细考论了谭元春在江西的交游,揭示了谭元春与江西诗风、文风相互影响的事实(第339-349页)。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重要问题的论述,几乎全部是在比较中完成。这包括竟陵派内部钟惺、谭元春的比较,其中涉及钟惺、谭元春年辈、仕宦经历、个性上等的不同,所导致的党争中钟、谭心态的不同,对文学之态度,也涉及两者诗风从早期“如出一手”到后期谭元春“避同调之声,厌争趋之陋”因而拈出一“阔”字作为钟惺诗学观念之补充,甚至不惜“由险涩以求深厚”的转变(第126页)。这使得竟陵派整体的演进、变化获得了更为丰富、更富张力和更合理的展开。这也包括更大范围和因素的比较。比如本书在解释明代成、弘至隆、万间,同样经历了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形态的发展及文学创作主体下移、区域文学骤兴,何以万历文坛“唯有楚地作家如此有意识地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来冲击前后七子所欲建立的明诗文正统地位”时,将之归因于李贽在此地的影响,本书指出:“重提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楚风”在万历文坛崛起的意义,在于透过地域文学的视角,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王学左派特别是李贽异端思想在当时传播的实际轨迹以及晚明文学接受上述哲学新思潮之影响的演进实态。”(第157页)。这已经是有关地域文学的一种总体的比较视野。又如论及钟、谭诗歌评点之学时,本书没有忽视元明以下如高棅《唐诗品汇》、冯惟讷《古诗纪》与《诗归》等在文献上的关联,但同时揭示了明代中前期复古派诗歌选评向以《诗归》为中心的竟陵派评点之学的重要转变,即“以个人主观鉴赏为中心的批评样式”的建立与直取作者“文心”的批评立场的建立。前者“进一步拓展与提升了评点的职能与地位,借此充分实现文学选集的文学批评功能”,从而“在中国评点学史上体现出崭新的划时代意义”,钟惺《诗经》评点,就沿着这个方向而开启了以文学家的眼光评经的风气;后者则发展出一种“以深心玄览察其‘幽情单绪’的细读工夫与领悟力”,“把握诗人及作品的内在精神脉理,重建文本”阐释方式(第418-419页),此种方式直接影响到金圣叹诗文评点。
如果说上述比较对于本书尚限于个案的或局部的效果和意义,那么作为竟陵派最直接、最重要的对话和反拨对象,其与“性灵派”的参照、比较则贯穿了竟陵派演化过程论述的全过程。本书通过后期公安派的转变,袁中道为救公安之弊而在诗风、诗学观念的转变,解释了钟惺何以会获得公安派中人的肯定、推奖(204页);通过对公安派先期对复古派诗风的扫荡、自我修正后的公安诗学与竟陵派的接近及公安派之后继无人等因素的论证,解释钟惺、谭元春何以在南京可以非常顺利地形成影响(第229页);而当竟陵派因《诗归》而风行天下时,袁中郎终于认识到其与竟陵派诗学宗旨之根本差异,其对《诗归》的批评,“毕竟告示了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公开决裂”(第283页)。本书不只看到竟陵派各时期文学主张欲矫“公安”之弊而有所树立的旨趣,也关注到了竟陵派形成、发展过程中两者更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比较,再加上与“后七子”“唐宋派”、闽中诗人,以及更早地与明前中期复古诗学的衔接、比较,竟陵派作为区域文学,在与时风迎拒、交游往复间形成全国影响的诗歌流派的过程,乃犁然可见,同时,本书也在实际上从一个特定角度,汇成了对整个明诗史、明诗学尤其是晚明诗史、诗学的统合的梳理和描述。在本书“新版后记”中,作者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方面对流派研究的功能进行阐述,他说:“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以来,文学流派研究一向被视作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阐释文学发展一种视角、方法,其研究范式的构建,因而直接关涉整个文学史体系的格局与内涵。在另一方面,相比较文学史而言,它可以是更为基础、更为本原,因而也是更为原创的研究,或许能更为灵敏地感受到面临的困境而即时予以调整、更新。”(第681页)因此,《竟陵派研究》是作者在学术积累较为成熟之期,体现作者学术理念的一部著作。本书亦孚其所悬之目标。
三
《竟陵派研究》之后,中观的和“明变求因”的观念、方式仍然是作者所有研究的重要特色,作者另外一部重要专著《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考察了由作为诗学“宗本”的严羽《沧浪诗话》出发,经由元明之际闽籍馆臣,而渐及于整个闽地的明代闽诗传统,其中涉及群体、流派、选本、央地互动等重要问题,自然是“明因求变”中观研究的好例,此种研究取向正如作者在本书“序论”中所言:“正因为地域文学自觉是近世文学发展的显著标志,那么,地域文学研究之于近世文学,其方法论意义不言而喻。”有关此种方法论意义具体的体现,作者接着说:“运用地域文学研究,从文学在某一特定时空生成、演进的实态着手,既注意该地域文学的特征,又进而探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整合过程,就能够为近世文学的重构拓展出纵深空间,从而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页)所不同的是,《竟陵派研究》是以流派为中心兼及地域、文体等的“明因求变”,《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则是基于地域而兼及其他的“明因求变”。而在重要问题的贯穿性思考上,发端于其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在《竟陵派研究》中有所表述的闽中地域文化(第254页),最终在《闽诗传统的生成》中得到充分展开。其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总体思考也一定对《现代中国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文明史学模式》(刊载于朱立元主编《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年第2期)一文有重要的启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翻出晚清、民国文学地理学背后的文明史学的存在,又据文明史学的原则、要素,对现代中国文学地理学相关研究及其特征作出阐释,其间对学科和领域间学理关联的把握令人赞叹。此外,如《<汉志>小说与方士关系探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则在《小说家出于稗官新考》(《中国古籍与文化论丛》2013年第12期)的基础上再向前追溯,将《汉志》小说与稗官,更重要的是与方士及其祭告山川之言辞行为诸环节串联起来,做一种较为彻底的文体“原始”研究,其虽为是个案探讨,但因综合引证的文献量之大、论证开掘之深,实质上也是“明因求变”的中观研究。而作者在《竟陵派研究》“余论”中对竟陵派诗风现代性的思考,则表明作者后来走向近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古今演变研究几乎是必然的。这些问题连缀起来,则是在文献的、问题的衔接和贯穿中构成了更大范围的“明变求因”。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代际差异之明显,精致的文本分析,大量的、自觉的理论介入,问题设置的高度理论化等,成为一时普遍的现象;即使是文化研究,由于“新文化史”的影响,也与传统文化研究颇相径庭,作者所感慨的“迄今又感受到时代发展、知识更新之迅猛,无论文学、史学,皆已面貌大变”(第684页),说的就是此种情形。所以,作者一方面对已有的包括“明变求因”的研究范式凝结、形成的过程,及其所具有的独特的、重要的文学史的解释力有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作者也必定敏锐地感受到现有研究范式所触及不到甚至遮蔽的研究命题,所以作者称:“一种已经积淀下来的模式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是否仍存在盲点,被统一性叙述筛汰的那部分历史该如何处置,这些恐怕是我们须不断自省的”(684页)。作者愿意留下一个学术“样本”,提供一个“批判的案例”(第684页),用意即在于此。因此,也是更重要的,作者希望通过对原有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的学术史的总结、反思,保持面对新的学术观念、方法的一种开放性,如作者所说,“我们重又行进至学术范式转换的十字路口”, 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流派研究如何再出发,寻求新的突破,同时也是为文学史研究探索新的空间”(第681页),甚至“做一种解构的工作以去蔽”,从而寻求“迈向‘事实’的有效途径”(第684页)。而此种开放性让我们期待将来一定会有新的中观的、明变求因的研究,在新的学术范式下展开,因为毕竟学术研究正是在新旧学术不断的切磋攻错中相互映照和不断推进的。那时候再来看《竟陵派研究》或者其他的反映一时代风尚之著述,评价其作为学术史“样本”的意义,也许能得到新的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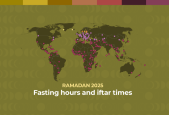







有话要说...